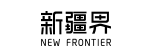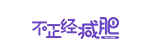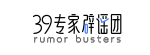爱情的男主角,他什么都有,有点钱,有点小能力,有涵养,有见地,另外,他还幽默,稳重,体贴。
他如此迷人,因此,他肯定还有一个爱他的妻子。
他什么都有,惟一没有的就是青春。
他惟一要向你索取的,也是青春。
亲爱的80女生,爱情是一种能力。这个已婚的毒药男人,他已经丧失了爱你的能力和权利。
爱你的人,他应该已经站成与你平等的姿态,或者,他正在跟着你的节拍成长。无论如何,去爱一个还有爱的自由,值得你爱的人。
别说爱不要结果。你正值青春,青春的花开完之后,没有结果会很惨,别说你不在乎结果,你输不起。
当然,你可以只是拿这一场花期当一场小小游戏,那么请你让路,相信爱情的人们,没空陪你。
生了虫子的老苹果那么甜
直到你离开我的时候,我还是不知道在你送给我的那摞露皇宣纸上写点什么。我埋头写下你的名字:应谦。我爱你。2005年6月11日。
你并不老,却有种长辈的暮气。而这种沉重的气质恰是当年我所需要的吧--刚刚在小恋人那里受到了伤害,我摒弃了那种笑出白牙齿的天真男孩,立即被你吸引。
你将一支烟当粉笔一样夹在食指和中指间,优雅的语言,你说:“台湾的作家里,女性的一位,我最欣赏朱天文。”
你后来对我说的话,也像朱天文的台词:“小珏,等你嫁的时候,我的卡你可以任意签,倾家荡产签光。”
今年我23岁,你34岁,等我嫁的时候,你大概也有40岁了吧。你们这代人和我们不一样,你们比较不在乎钱,而我却很在乎。为什么呢?大概是因为我们需要钱,因为我们穷。我不仅物质上因年轻而缺乏,精神上也一样十分穷困。
我渴望爱情,于是四处出击、寻找,可是往往找到的并不是完美的爱情。像是一只刺猬,年轻健康却很饥饿,它到处寻觅苹果,可最甜的一枚却生了虫子。
你就是那只生了虫子的老苹果。
你给我爱情,却不能爱我。因为你有了一个家,你的爱得分散成亲情、责任、道义分给你妻子和儿子。
于是你便给我钱,你顺着我的性子纵容我,从不违拗。你买了很多钻石给我,买了很多衣服给我,你甚至把私房钱拿出来给我的房子付了首期。一切看上去就都合情合理了,我成了你的情人。
我知道你这是在为有一天你离开我做打算,你想让我生活得好,不至于在失去爱情的同时在物质上也变得匮乏。你的好意我知道。
我便统统接受。我还能再怎样呢?我是那么爱你,我明白骨子里你是一个好人,只有好人才会受着这种折磨,若是坏人你一定会娶我,因为坏人对家庭没有责任心。
于是,越发是这样,我们的爱情越猛烈。
我喜欢枕着你的大腿看着你的下巴,对你说:“别去想将来吧。”
我们就是这样彼此鼓励劝勉,才一起走到了这一天,带着我们华丽的无耻,以及很多的无地自容。
有什么不可以呢?我时常这样问自己,得到的回答是:当然可以。
2005年4月,报纸上传出朱天文与侯孝贤的绯闻。新闻不大,但我却一直记着。因为朱天文是你最喜欢的作家,却是我最讨厌的女人。
朱天文,1956年出生于台湾高雄。侯孝贤比她大7岁。一起合作《小毕的故事》时,她是编剧,他是导演,不伦之恋大概由此而生。
很像我们的关系,你比我大了还不止7岁。
这么说来,我最讨厌的不是朱天文,而是我自己?
可我却深爱你。
沉默如谜的呼吸
第一次见面,约在上岛咖啡。
我穿了吊带的热带花卉连衣裙,细高跟凉鞋,自以为风姿妖娆。但很快我便知道自己错了,男人的蜜糖,往往是女人的砒霜。
“看得出来你很寂寞。”冯琳坐在我对面,这个35岁的女人胸有成竹地微笑道。她戴着金丝边的眼镜,衣着简单而干净。我想反驳,但是无从下手,我一直以为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而已。
分别时,我看见她坐在出租车的前座,手很自然地搭在车窗上。我不知道她这种踏实感从何而来。我从来都是只坐后排,双手谨小慎微地抓着包。这也许就是我们对待爱情,对待男人的态度。
此时,距她第一次拨通我的电话,已经整整四年。
惟一的变化是我从22岁来到了26岁,而不变的是:我,冯琳,她的丈夫明徽,我们三个人平静的、微妙的、四年如一日的拉锯战。这场战争何时结束,我不知道,也许就是明天,也许还要熬过四年。
四年前,在我租来的小屋里,在清晨越来越清晰的光线中,我开始害怕,不知该怎样面对这个男人。那时我刚考上研究生,而他的身份是已婚。我侧着身子把头埋进被子里,不敢看他。他轻轻地把被子掀开,笑着问:“你吃几个煎蛋?”我听着厨房的响动,披衣下床,看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系着围裙往锅里倒油。一边用一只手熟练地敲开鸡蛋,再把壳准确无误地投进垃圾桶。我站在门口,听见鸡蛋“呲啦”一声在锅里炸开,炸出满屋温馨的香气。
我开始沉默而简单地爱上了这个男人。他会往我的菊花茶里多加一块冰糖,会买各种大小的泰迪熊当礼物,会揉我被高跟鞋打得生疼的脚。我对他说过,我并不在乎他是否结了婚。但谁都知道那是假的。我也慢慢地知道,原来每个男人心里,都希望有个花园,里面种着各种红白玫瑰,如果可能的话,不要给他们开始培育的机会。
冯琳第一次给我打电话,是四年前的深夜,当时我在学校的元旦舞会上,望着这个在心里默记过几百遍的座机号码,慌得手足无措。一抬眼,他正在很远处落寞地坐着。手机一再地响,不接,再响,再不接。宛如漫长的马拉松,那晚的电话长跑,我是赢家。
在我和明徽为他离不离婚大吵过后的第二天,冯琳的号码再次跳跃在我的手机屏幕上。我赌气般按下接听键,准备好了一切说辞,但电话那头竟无人说话,似乎有一丝呼吸声隐隐传来,然后就挂断了。这呼吸声沉默如一个谜语。我并不了解这个女人,和属于她的世界,我与她沟通的惟一方式,只有,一再伤害她。
我和她,究竟会得到怎样的补偿,这个答案已经藏匿了四年。也许明天就能揭晓,也许,会在我们心中存留一辈子。
(实习编辑:李梅)
39健康网(www.39.net)专稿,未经书面授权请勿转载。

 39健康网
39健康网 男人早泻是什么原因
男人早泻是什么原因 男人早泻是怎么回事
男人早泻是怎么回事 男人脚发凉是什么原因
男人脚发凉是什么原因 男人征服女人需做好
男人征服女人需做好 男人早泻会有什么症状
男人早泻会有什么症状 看!男人最容易“偷腥”的时间
看!男人最容易“偷腥”的时间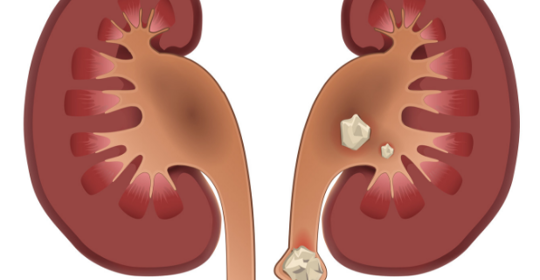 为什么得肾结石的男性越来越多?跟3种食物有关,你可能也天天吃
为什么得肾结石的男性越来越多?跟3种食物有关,你可能也天天吃 男人能坚持多久才算正常?这个时间让人意外
男人能坚持多久才算正常?这个时间让人意外 男人在夫妻生活后,睾丸疼是怎么回事?
男人在夫妻生活后,睾丸疼是怎么回事?